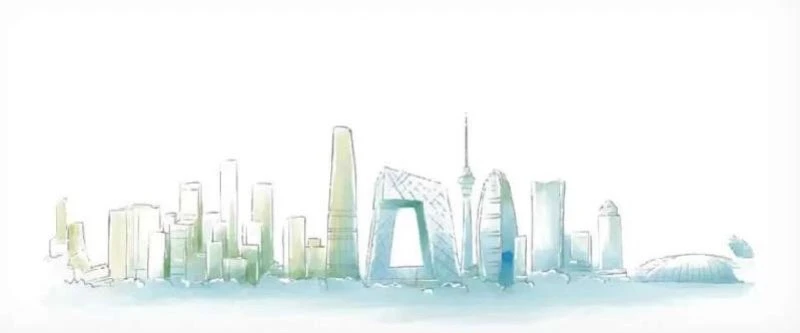老杨来到北京的时候,我不知道我是应该留在北京,还是离开北京。
当时北京工厂财务总监位置出现空缺,我以为领导们考验我已经考验够了,顺手就把这块月饼赏给我了。结果,天上掉下个杨大哥,成了新任财务总监。
我按照工作流程给他各种交接,心里各种不忿:我每周工作八十个小时,流程管理之外还飞去中国各地打补丁,谁家缺人我都去抗一阵儿,任劳任怨。现在有机会了却不给我,实在是欺负人。
老杨四十多岁了,中等个子小眼睛。他好像从来不会着急,跟谁说话都笑容满面,但绝不让人觉得他在巴结谁。他的笑容是给所有人的,不管对方是总经理,还是车间工人。
没来多久,老杨已经把全厂人头都认熟了。跟人打招呼有名有姓,称兄道弟,好像他在这里干了一辈子似的。我想起来以前M公司的管理者培训,老师讲的话果然不错,大家喜欢自己的名字;把别人名字叫对了,是管理者的基本功。有例为证,人家老杨才来一个星期,比我受欢迎多了。
老杨玩起电子表格来不算灵光,本来公式一个套一个就够乱的;最近总部又做了一些改进,整套系统更加复杂。老杨的小本本记得满满的,依然不得要领。我叹口气:“这个月我给你做,你在边儿上瞅着。下月你得自己做啊。我还不一定在这儿呢。”
老杨连连称谢。活儿干完,老杨说:“别回酒店吃你那个客房送餐了。我带你换个地方儿,咱们去牛街。”
那天吃了一堆特色美食,外带打包。的确比那些貌似高端的商务餐饮好吃多了。我们转悠够了,找了家茶饮店坐下。我跟老杨说:“今天玩得高兴,以后你不欠我了。”

老杨说:“下次咱还来,我把我老婆儿子也叫上。今儿有点晚,她们吃过饭了,就没来。”
我这才知道他是北京土著。老杨说他在长春工厂奋战四年了,期间多次要求调回北京。家里这么多年全靠老婆一个人打理,一晃儿儿子快考高中了;老婆下了最后通牒,再不回来,就甭回来了。
老杨说:“明白了吧?有时候咱老板没给你一样东西,是因为他有难处。”
我说:“老板的难处我刚知道,可我的难处老板一直知道啊。”
老杨想起来了,“你下午提了一句,在这儿不在这儿的话,有下家啦?”
我不敢完全交底儿,没接话茬。老杨说:“我不想多打听啊。就一句话,做生不如做熟。你信不信,我忍的年头比你长。”
那时候我还真有两份新职位聘书我在手中,不用面试,全是M公司的前老板们推荐的。前男友可能不喜欢我,可是前老板们毫无例外地喜欢我。这些聘书便是明证——他们都想带我去新公司,薪水头衔都极其诱人。
我原本梦想着大步跨进老板的办公室,把这些聘书排在他眼前,薪水部分用马克笔强调一下,再奉送辞职申请书一份请求签字……
然后呢?就这么走了?谁家的乌鸦不黑?现在我明白老板也有难处。换了我,我好意思继续让老杨戍守边关?
那时闲居京城,我无事便读《京华烟云》《四世同堂》,时不常地去老胡同溜达,去潘家园旧货市场走走,连鲁迅故居我都去看过。我喜欢北京,就是因为这份古韵闲情。这份喜欢和老杨家里实实在在的生计相比,实在太轻飘飘了。
《京华烟云》里姚先生笃信道教,崇尚应时而动,礼法自然。既然我不知道该做什么,那就什么都不做,以静制动好了。
例行电话会议的时候,我把关键数据写在本子上,帮老杨过了第一关。他还是肯努力的,从那以后逐渐全盘接手。
当时的北京工厂规模尚小,办公地点略嫌狭窄。我挺自觉地把财务总监的办公桌交还老杨,搬去小会议室办公。有一天进来一拨儿工程师,明明看我坐着角落,理也不理就开始他们的小组会议。中间夹杂着笑谈,这群清华的同学侃起来也是有荤有素,没完没了。
我的报告写到一半,被他们一搅合,顿时失去了思路。明天报告到期啊!也怪我自己不争气,一有人说话就支着耳朵听着。我忍着,看他们什么时候结束。一个工程师跑出去一趟,居然给每个人都泡了杯咖啡用托盘端进来了,这是要持久战啊!
我问他们:“你们预定会议室了吗?”
他们挺惊讶,“什么时候有这规矩?空了就进来呗。”我一听火大,“我在这儿坐着呢,会议室怎么算空的?”
他们也不当回事:“那你出去找个地儿呗,我们这么多人呢。”
老杨正从门口过,赶紧帮我收拾文件夹,“走走,去我那屋。”
老杨说:“怪我不周到,你以后在我这儿凑合凑合算了。清华那帮工程师可齐心了,你最好别得罪他们。精益生产项目指着他们呢。”
老杨多走了十几年的路,果然面面俱到,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修炼到他那个地步。
清华的同学们大多不拘小节,这等小事没人在意,我们后来依然合作愉快。只是跟老杨合用办公室诸多不便。
有一回我听了会儿刘天华的二胡,忘了戴耳机,老杨头一次提意见,“咱换点儿别的行不?我心里一悲痛,什么都做不下去了。”如果谁有电话进来了,内容比较机密的话,就得马上出去接。

有一次我没来得及走,座机上有个电话会议,我和老杨都得挂在线上。我手机上进来的电话是中国区资金部总监打来的。他指示我把一个工厂的贷款两千万存到他指定的银行,还要定存一年。
我胡乱应了一通,觉得哪里不对。工厂贷款那是有指定用途的,否则付六个百分点的贷款利息做什么?费半天劲贷款,然后存另一家银行拿三个点的存款利息,这不是有病吗?好像街上随便拨拉一个脑袋都能算过来这笔帐。刚才资金部经理还嫌我脑瓜儿不够使,我看他才是脑子进水呢。
我跟老杨商量,老杨也百思不得其解。不过他提醒我一句,资金部头头跟他老相识了。那人脾气大,气量小,只是关系过硬。我要是跟他对着干,只怕吃不了兜着走。
我问,“咱们就当这两千万是两万,这钱是自个儿的,你会这样处理?”老杨说,“我要敢这么瞎折腾,我老婆得削死我!”
我说:“那不结了,我得告诉亚太的大佬们。谁家的钱都不该这么花。要是这点帐他们都倒腾不明白,我就把那两份聘书用上直接走人,不跟他们混了。”
老杨倒是不含糊,“那我给你做个旁证。先问问,你那俩位置还有吗?都在北京吧?反正你也用不了俩聘书。万一出事了,你挑一个,剩下那个给我,行不?”
我俩联手发出电子邮件给我们的直线汇报老板,同时抄送若干给曲线汇报老板以及亚太头头张总,然后静待靴子落地。老杨还挺泰然,该干啥干啥。人家说了,只要不出京,哪儿干都一样。
等了又等,没听到有什么指示。既然没有最新指令,那个工厂就按原计划把贷款用于设备升级改造,我们也渐渐把这事儿放在脑后。
几个月后,资金部总监调任闲职,照旧从公司领他的高薪。老杨跟我瞎猜,也许他的确有别才,我们未能发现?还是老板们又有一肚子苦衷,不能动他?老板的心思很难猜,大概我们不需要懂。
我在北京的流程整改项目接近尾声,忽然接到任命,要我负责亚太区的内部控制审计,工作地点转到上海。这次总算姨娘扶正,和财务总监平级了。老杨替我高兴,又有点担心,“这个活儿出差太多,又得罪人,以前都是男生做的。你真的想接?”
我说:“有挑战性的活儿,我才想试试。回头儿我让你看看,女生怎么做这个位置。”
老杨又提醒我,“别光看头衔,关键是钱要给到位,别的都是次要问题。”我看过了,钱给的也挺到位。
践行宴上,老杨很开心:“这下我终于有自己的办公室了。你走了,我才踏实了。要不我老担心,你就坐边儿上,领导们换我实在太方便了。反正北京的内控也归你管,你什么时候想回娘家就回。我就不下帖子请啦!”
我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,跟老杨打交道几个月,他什么时候都不玩儿虚的。
餐厅里暖气给得很足,温暖如春。那天的北京没有寒风,窗外的雪轻轻飘下,地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,像极了恋爱场面用的雪。这般景象,在江南怕是看不到了。
中国之大,北京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像家乡的城市。可惜北京不是任何人的北京,北京只是它自己,历经千年风霜,静静矗立原地。无论是古今将相,还是风流人士,都是过客。我和北京有一年的缘分,对此,我很知足。
我举杯敬了敬老杨,心里轻轻说:“再见了,北京。”